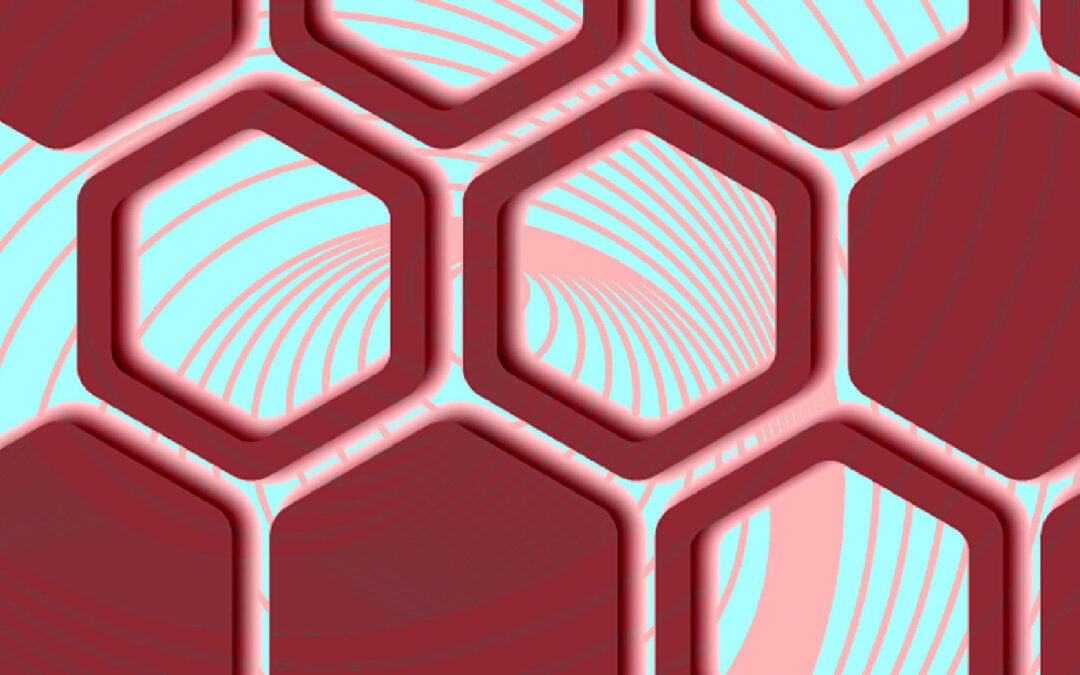童年学研究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反思,该领域的知识生产反映了全球北方的霸权主义,而全球南方产生的观点被压制和排斥。源自全球北方的理想化、标准化的童年,强化了对全球南方童年的假设和偏见。全球北方世界所构建的理想的童年框架,通常被描绘成“白人”和“中产阶级”,使得来自全球南方世界的儿童被误解为是弱势的、被剥削的、需要被拯救的 (Hanson et al., 2018), 而这则会产生对南方童年的偏见 (Kesby et al., 2006, p.186)。
在全球南方的农村童年这一领域中,这种偏见尤为明显。尽管对农村的关注不断增加,研究人员通常关注全球北方/西方国家的童年。但对于农村童年的研究,特别是在全球南方,是有限的 (Panelli et al., 2007)。人们倾向于将全球北方的农村童年浪漫化和理想化,而将全球南方的农村童年病态化 (Panelli et al., 2007; Kesby et al., 2006),这种对农村儿童的假设和刻板印象反映了西方理想化的童年对全球的影响。
为了更全面地树立一个关于全球南方农村童年的理解,我与三位童年研究学者进行了交谈,同时这也作为我在伦敦大学学院(UCL) 本科期间在Reimagining Childhood Studies项目实习的一部分。Rachel Murphy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教授。她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因城市化发展和人口流动而引发的的社会变化。Afua Twum-Danso Imoh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全球儿童和福利的高级讲师,研究重点是西非的儿童权利和童年。王友缘是上海师范大学儿童早期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她目前主要研究童年社会学,以及中国童年观念的变化。
在下文中,我将把我与每位学者的讨论交织在一起,以强调儿童研究的三个关键见解。首先,在大众话语和许多学术著作中,全球方农村的童年往往被视为悲惨和匮乏。其次,关注童年的多元性可以开辟理解农村童年新的途径。最后,我提出我们需要挑战当前的知识生产,承认农村童年经历的多元性。
假设的“脆弱”
在访谈中,我以中国的留守儿童为例,讨论了对农村童年的表述和关注。在中国的背景下,”留守儿童 “通常被定义为那些留在农村地区,而他们的父母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儿童。由于内部迁移,中国大约有7000万留守儿童(Yiu & Yun, 2017)。Rachel、Afua和王友缘教授指出,中国的留守儿童经常被公众贴上负面的标签。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且农村相对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 他们被视为弱势群体。三位学者针对影响留守儿童和农村儿童的背景因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提供了更全面的看法与理解。
首先,在探讨留守童年经历时,Afua认为缺少来自祖父母和大家庭的视角。她呼吁关注儿童更广泛的生活背景,而不是简单假设留守儿童因父母的缺位而产生一系列问题。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被视为优先于其他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需要关注儿童从大家庭中收获的亲情。儿童也与其他人建立关系,但往往核心家庭被认为可以最有效地照顾儿童。”
同样,因为王友缘教授和Rachel都在中国农村进行过民族志研究,她们提到留守儿童大部分时间是和祖父母或近亲在一起,并描述了儿童与祖父母建立的情感上的亲密关系。Rachel提到:
“很多学术文献中强调儿童与父母分离,虽然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强调,然而,它也忽略了这些儿童与祖父母建立的情感关系,或者儿童与祖父母之间已经破裂的一些关系。”
理想化的家庭规范,即孩子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是由中国城市和全球北方的主流童年框架形成的,一些武断的标准使得人们缺少对农村童年的思考。
Afua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即认识到在父母迁移之前儿童与他人建立的多种亲情关系。她认为孩子和祖父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可能不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结果,而是一种预先存在的关系;然而,当祖父母成为主要的照顾者时,祖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
除了在假定的贫困和脆弱,以及对大家庭生活背景认识不足外,Rachel和王友缘教授还强调了留守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所面临的选择、挣扎、与挑战。
“因此,‘呼吁建立家长、学校和社区的三方联盟’ [媒体关于父母从农村地区迁移时社会应如何支持儿童的说法] 忽视了父母经济、文化和时间资源的缺乏。它忽略了父母面临的选择,或在为赚钱抚养孩子、养家糊口方面所面临的艰难选择。” (Rachel Murphy)
“当你真正从他们的角度理解他们的经历时,分离可能是唯一和最佳的选择。对孩子和父母来说,这种独特的留守经历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消极的,有的时候可能是积极的。它可以转化为一种向上的力量,会持续伴随着他的。” (王友缘)
因此,在中国农村背景下,关于留守儿童的成长,很难得出绝对负面的结论或进行简单的假设。即使有 “留守”的共同经历,背景和个体差异也会导致童年的经历不同。同时,由于中国留守儿童的话题受到大众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他形式的中国农村童年常常被忽视。在采访中,三位学者认为在进行跨地域和跨文化背景的研究时,需要意识到并且承认农村童年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童年的多元性
在研究不同背景下的童年时,了解儿童自己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化背景、当地背景和他们所处的情况是至关重要的(Spyrou, 2017)。在这方面,我采访的学者们分享了三个独特的观点。
首先,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王友缘教授强调了留守儿童群体中存在的个体差异。在她的研究中,来自同一个农村家庭的两个孩子对自己的留守身份和农村身份持有不同的理解,姐姐在初中无法毕业的情况下仍然努力追求成功,而自愿离开高中的弟弟和姐姐相比,显得动力不足。王友缘表示:
“我认为农村的童年,留守儿童的童年,是非常复杂的。个体的因素在里面起到很大的影响,不能简单的提出一些结论。”
王友缘教授进一步介绍中国的历史背景,以解释西方的童年视角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
“现代化的、西方化的童年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引入中国。它的这种霸权性的存在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是联系在一起的。到了后来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这种西方的现代童年观通过学校教育的再生产,得到了加强。”
她接着在中国城市的童年和西方构建的童年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这也成为一种趋势,中国城市父母会向西方学习,农村父母向城市父母学习。”
被父母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所重视的主流童年观念,可能会限制我们对农村童年的认知和理解。王友缘强调,对童年需要有更多的批判和反思,她认为这需要更多来自全世界的互动和交流。这不仅对研究农村儿童的中国城市研究者来说是必要的,对研究来自陌生文化的童年的研究者来说也是如此。
除了农村留守儿童,Rachel指出,由于中国对农村和城市的重新划分,城市留守儿童的数量越来越多。
“我认为人们强调农村情况下的留守儿童,但这与更广泛的城市化进程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城市留守儿童的现象正在增加。”
因此,留守儿童不仅是一种农村现象,而且正逐渐成为一种城市现象。此外,她还强调了城市对农村儿童童年经历的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留守儿童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孩子在城市里和父母一起过暑假,假期结束后再搬回农村。”
王友缘教授和Rachel关注点集中在中国留守儿童童年经历的多元性,而Afua则提出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中国农村童年的主流形象。她随后指出,这不仅是由于全球北方的影响,全球南方的本土研究者也认同全球北方的观点,这促成了对留守儿童代表 “贫穷 “童年的一元化的关注。
“在中国,还有其他的农村儿童,他们没有留守的经历,但由于被边缘化,可能会有经历与留守儿童类似的成长。同时,也有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童年。我们不一定会看到这些不同类型的童年,因为很多研究都集中在贫困儿童的生活上。”
作为非洲童年的研究者,Afua表示农村童年在加纳背景下也被理解为“不足的,缺乏的”。
“我想说的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也是如此。大多数研究是基于农村儿童和他们生活中的匮乏。其中也包括了城市的流浪儿童和童工。然而,也有其他类型的童年。例如,在加纳,有一些儿童也很贫穷,但并不生活在边缘,也有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儿童,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障碍。我们没有看到那种多元化的童年经历。”
这反映了全球北方视角在童年知识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的问题,Afua建议应通过发展对全球南方农村童年的多维关注来挑战这一问题(Twum-Danso Imoh等人,2019)。理想化的全球北方框架的内化导致研究人员主要关注农村儿童的偏差,而没有注意到童年经历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总结思考
全球南北的二元对立形成了对全球南方世界的农村童年的一些偏见与假设。为跳出全球北方和南方的二元视角,研究人员需要承认世界各地童年的多元性,并通过背景,社会环境,和关系的视角理解儿童生活的复杂性。有人建议,研究人员作为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要去伪存真,通过倾听儿童参与者的声音,考虑儿童本身以外的更广泛的因素和影响,来开辟新的思维方式,塑造他们多样的童年经历(Pain,2010;Spyrou,2017)。
作为童年学研究领域的初学者,我起初关注中国的留守儿童,是因为公众对农村童年的关注,和媒体对这个群体的广泛报道。我的看法也受到先前的知识和对农村儿童生活的负面假设的影响。与Rachel、Afua和王友缘三位学者的交谈,激发了我的思考,我学会了通过考虑塑造不同经验的个人、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来跳出对南方童年的原有假设。更重要的是,这些访谈表明了农村童年的动态和复杂性。”农村 “是童年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需要进行进一步解读、辩论和理论化。农村童年经历的多样性表明,我们还需要探索和研究儿童如何构建他们的农村身份以及他们的生活如何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为 Reimagining Childhood Studies 项目带来不同的视角,以鼓励跨学科的对话。
Reference List
Hanson, K. et al. (2018) ‘“Global/local” research on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a “global society”’, Childhood, 25(3), pp. 272–296.
Kesby, M., Gwanzura-Ottemoller, F. and Chizororo, M. (2006) ‘Theorising other, “other childhoods”: Issues emerging from work on HIV in urban and rural Zimbabwe’, Children’s Geographies, 4(2), pp. 185–202.
Panelli, R., Punch, S. and Robson, E. (eds) (2007)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ural Childhood and Youth. Routledge.
Pain, R. (2010) ‘Ways beyond disciplinarity’, Children’s Geographies, 8(2), pp. 223–225.
Spyrou, S. (2017) ‘Time to decenter childhood?’, Childhood, 24(4), pp. 433–437.
Twum-Danso Imoh, A., Bourdillon, M. and Meichsner, S. (eds) (2019) Global Childhoods beyond the North-South Divid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Yiu, L. and Yun, L. (2017) ‘China’s Rural Education: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50(4), pp. 307–314.
Cite as
Jiahao Zhang, ‘Exploring Plurality – Rural Childhoods in the Global South,’ in Reimagining Childhood Studies, 20 July 2022, https://reimaginingchildhoodstudies.com/全球南方的农村童年/